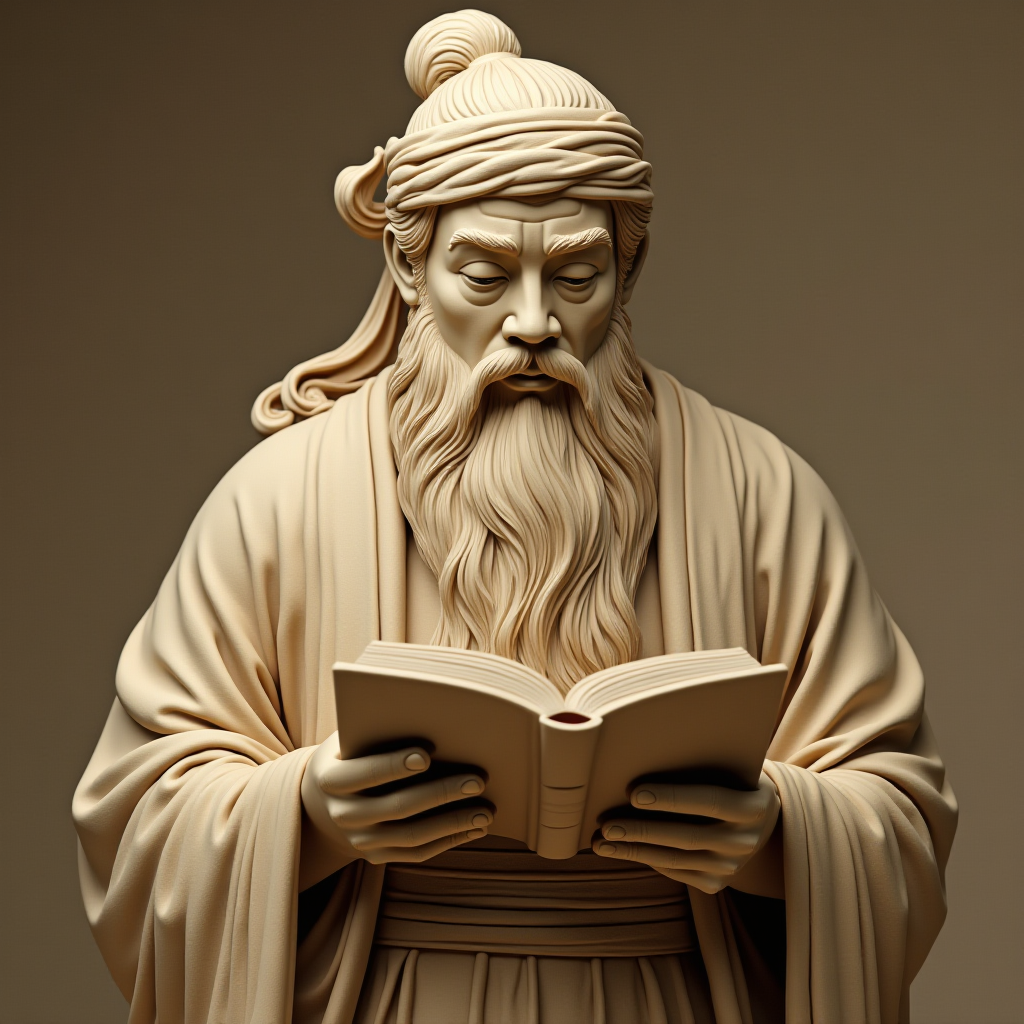在2019年出版的《劍橋詮釋學手冊》(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rmeneutics)一書中,第十二章名為〈詮釋學:非西方的進路〉(Hermeneutics: Non-Western Approaches),[1]作者馬愷之(Kai Marchal)指出解釋經典傳統和解釋理論在非西方世界已有悠久的歷史,包括印度、阿拉伯、猶太、日本、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的經典詮釋傳統。但為甚麼這一直被西方學界所忽略?
馬愷之認為這是由於西方先行現代化,又經過了殖民地時代所致。西方學界又會認為非西方的經典詮釋傳統只屬於宗教性質或只限於「地區性質」,與具普遍意義的理解問題無關,只視為是文獻學的範圍。[2]而受西方訓練的學者對「比較哲學」和「全球哲學」抱極懷疑的態度,故此只視非西方學者為語言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或視為宗教學家和文化研究等。為甚麼會這樣?馬愷之認為這是源於西方學界的偏見和含糊的假設,對東方哲學傳統欠缺認識所致。他認為東方的進路與歐陸的哲學詮釋學有相似的地方。[3]
因馬愷之是專門研究中國哲學,故他在〈詮釋學:非西方的進路〉一文中列舉了孟子、王弼和朱熹[4]詮釋《論語》的觀念作為例子,說明與歐陸哲學詮釋學相似的地方。雖然文中仍採用西方的哲學理念作對照,但馬愷之正確地指出我們不應用歐美的世界觀去把握中國的詮釋傳統,並把之同化,而忽略了兩者之間在文化和歷史上的差異,最後成為了西方理論的注腳或完善。[5]
西方學界對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重視和肯定,正好回答了沙馬達(Stanley J. Samartha)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表達的憂慮:「依賴與亞洲生活相異的國家所建立的詮釋規則,會妨礙教會的成長,因它減少我們的可信性,削弱我們的士氣,也曲解耶穌基督的普遍性,有違聖經的見證。」[6]
筆者認為華人教會依賴西方聖經詮釋學主要有三個歷史原因:
一、西方詮釋學是從聖經詮釋發展出來的,聖經詮釋與西方詮釋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材料豐富。但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詮釋學已從針對詮釋聖經轉向一般文本,是屬非基督教的詮釋學了。
二、歐美教會確是華人教會的屬靈師傅,華人素有「尊師重道」、「一生為師,終生為父」的傳統,向前輩學習是合情合理的。但基督教來華200多年後,歐美教會已步入後基督教時代,而華人教會卻持續發展,擁有博士學位的華人聖經和神學學者(包括中港台)為數已不少,華人教會應積極建構本土聖經詮釋學和講道學才合理。此舉不單有利於信仰本色化,幫助華人教會本身的發展,更可反過來幫助西方教會,豐富其對信仰的理解和實踐。[7]
三、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為了救國和追求富強,掀起了一股「全盤西化」之風,竭力吸收西方的科學和民主,輕看或甚至否定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不願花時間去研究和理解,凡事以實用為主要前提。周國平對此現象有深刻的觀察:
「百年中國的主題是富強。為求富強,人們到西方尋找真理。在這個出發點中蘊涵著中國文化的一個悠久傳統,便是把真理僅僅當作了工具,對於任何精神事物唯求其功用而忽視其本身的價值。……人們常常嘆息,中國為何產生不了大哲學家、大詩人、大作曲家、大科學家等等。據我看,原因很可能在於我們的文化傳統的實用品格,對純粹的精神性事業不重視、不支持。一切偉大的精神創造的前提是把精神價值本身看得至高無上,在我們的氛圍中,這樣的創造者不易產生,即使產生了也是孤單的,很容易夭折。」[8]
周國平對中國人性格的觀察同時也解釋了為何華人教會欠缺本色化這種創造思維的動力。直接抄襲別人的東西是最快取得即時成效的方法,因為不用花時間精力去研發。筆者認為華人教會也因受其民族性格影響,凡事都是以實用為主,找現成的東西抄抄改改最省時省力的。引入歐美教會的東西就最簡單,節省自行研發的時間和資源。
以現今華人教會在各方面條件來說,都應該有能力去從事更多本土化、處境化的創新工程,不用盲目跟從和依賴西方教會的了。中西教會應可達到彼此學習、彼此尊重和互補不足的平等位置。
總而言之,華人教會可透過取材於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來建構本色化的聖經詮釋學和講道學,深化華人教會對信仰的理解和實踐。這也就是為何現今就是創建華人講道學的時機了。
[1] Kai Marchal, “Hermeneutics: Non-Western Approache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rmeneutics, ed. Michael N. Forster and Kristin Gjesd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286-303.此書不是關於西方詮釋學的歷史,而是探討現代詮釋學的發展趨勢和對不同範疇的影響。每一章由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撰寫,包括哲學、文學、歷史、法律和神學。雖然現代詮釋學是源自德國學界的努力,更是從聖經詮釋為發展成為具普遍性的一般詮釋學,但編者卻認定了非西方詮釋學的進路是其中一個發展方向之一,並以中國的經典詮釋作為代表。
[2] Marchal,“Hermeneutics: Non-Western Approaches,”287-88.
[3] Marchal,“Hermeneutics: Non-Western Approaches,”288.
[4] 就「經典詮釋」而言,朱子不僅注群經,也有不少反思「為何注經」的論述,以及一套關於注經的方法論。所以海內外學界對於朱子的研究是最豐富的。參李明輝,〈李序〉,《朱熹與經典詮釋》,林維杰著(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iii。
[5] Marchal,“Hermeneutics: Non-Western Approaches,”290-93.
[6] 沙馬達,〈亞洲的處境:素材與方向〉,余卓豪譯,《亞洲處境與聖經詮釋》,李熾昌主編(香港:基督教文藝,2000),11-18。但沙馬達為了與聖經以外的亞洲經典文本可以平等對話,彼此豐富之同時,卻把它們的權威與聖經等同。筆者對此有所保留。
[7] 美國韋恩‧科迪羅(Wayne Cordeiro)牧師曾分享他到中國湖南省培訓家庭教會領袖的經驗。他表示欽佩中國基督徒即使面對政治迫害也仍堅守自己信仰的真實性,熱情和激情。並認為美國信徒要向中國信徒學習。見Thor, “Amazing Story About Chinese Underground Churches,”https://christianlifetoday.net/chinese-underground-churches (accessed February 14, 2020).
[8] 周國平,〈東西方文化〉,《愛思想》(2009年10月4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656.html(取自2020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