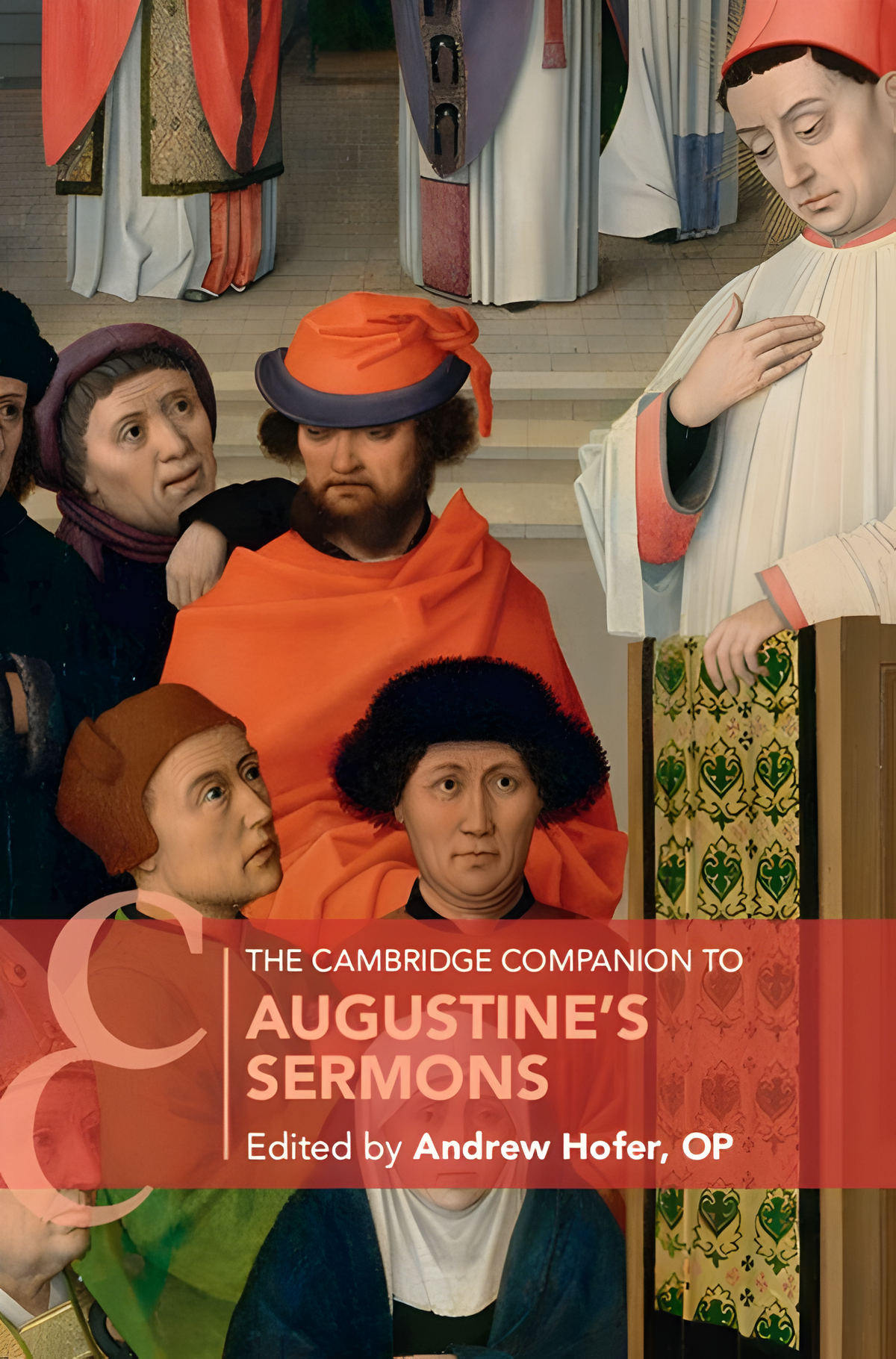在華人語境中,「宗師」一詞代表著備受尊敬、值得效法的師者,而「一代宗師」則進一步凸顯其對一個時代乃至跨越時代的深遠影響和文化精神的象徵性。以此標準衡量,奧古斯丁(354-430年),無疑是講道學領域中的一代宗師。他不僅是教會歷史上首部講道學教科書《論基督教教義》(De Doctrina Christiana)的作者,更是一位經常講道的主教。據估計,他一生講道約六千次,現存的講章約有近九百多篇。奧古斯丁的講道都被譽為深具靈魂觸動力的典範。無論是他的著作還是講道實踐,都深刻影響了講道學的發展,甚至在當代講道學中,依然可以見到他思想的身影。
西方教會講道學的奠基人物
奧古斯丁因其在神學教義上的卓越貢獻而被尊崇為「教會四大博士」(Doctor of the Church)之一,然而,這種高度評價往往使人忽略了他同時也是基督教講道學領域的奠基性人物。
教父神學學者華倫‧史密斯(J. Warren Smith)曾直言:「奧古斯丁研究(Augustinian Studies)的一大弔詭,在於學界對其講道工作的關注相對薄弱。儘管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詳盡論述其修辭學訓練與教學經歷,這些早期修辭訓練的成果卻長期被忽視。學界似乎預設,奧古斯丁作為基督教哲學家與神學家的著作——如《懺悔錄》、《上帝之城》與《論三位一體》——才是真正展現其天才、具有永恆價值的經典,而講道則僅是希波主教在撰寫深奧神學論文之餘,必須履行的例行職責之一。」[1] 奧古斯丁深受古典修辭學(即演說技藝),特別是西塞羅學派(Ciceronian)的影響,並將其修辭理論加以轉化,使之成為教會宣講與教義傳遞中可運用的重要工具。[2]
講道學者凃偉文精確指出:「講道學與修辭學從第四世紀開始,因著奧古斯丁著作《論基督教教義》的倡議,就已經締結了深刻的夥伴關係,教會的傳道者一方面從聖經與神學發掘講道的內容(content),另一方面則從修辭理論中習得傳講信息的形式(form)。這個形式與內容的結合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都沒有太多的改變,……新講道學對講章形式的再思其實重現了古典修辭理論中看重內容與形式的融合。」[3] 事實上,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興起的「新講道學」(New Homiletics)運動,其理論基礎與實踐方法,亦無法脫離奧古斯丁講道學的深厚影響。
重新發現奧古斯丁的講道價值
自二十一世初以來,隨著對奧古斯丁講章新原典的發現與翻譯、以及文本傳播學、修辭學和牧養神學等跨學科關注的興盛,奧古斯丁講道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今年五月出版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s Sermons正是此一學術熱潮的最新成果。該專著由十六位國際奧古斯丁學者共同撰寫,各自負責不同主題章節,全面呈現奧古斯丁講道的多維度研究。[4]
此文集探討了奧古斯丁講道學中的多重課題,涵蓋他作為牧者的講道使命,講道中對聖經文本及教會節期的詮釋,以及其講道中呈現的核心神學與倫理主題。這本書呈現奧古斯丁如何在講壇上將聖經教義與基督徒生活緊密結合,表達對教會和基督徒共同體的關懷,並展示他透過講道引領信徒靈命成長與倫理實踐的全貌。換言之,本書不僅是對奧古斯丁講壇文字的學術檢視,更是深入理解其教會牧養與神學思想的重要窗口。奧古斯丁的講道現已成為當代奧古斯丁研究的重要分支,值得華人教會與學術界予關注。
教會歷史第一本講道學教科書《論基督教教義》的誕生
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 ( Emperor Theodosius I, 347-395) 於380年頒布《帖撒羅尼迦詔令》(Edict of Thessalonica),正式將基督教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標誌著基督教時代(Christian Era)的開始。他也於391年和392年頒布嚴格法令,禁止各種異教活動,強化基督教的統治地位。
奧古斯丁就在這大時代於395年當上希波主教(Bishop of Hippo),他要帶領教會展開了一連串鞏固和優化的工作,包括制定教會的權力架構、定立教義和信仰內容、恆常化崇拜聚會、建設教會標記、提供退修場所和翻譯更佳的拉丁文版本聖經等。[5]
作為主教,奧古斯丁肩負帶領教會抵抗異端威脅的重任,特別面對摩尼教派( Manichaeans )、伯拉糾派( Pelagians )、多納徒派( Donatists ) 和普西利安派( Priscillianists ) 的攻擊,教義的確立變得尤為迫切。他致力於訓練神職人員,教導他們以正確的聖經詮釋方法來解經,並有效捍衛教會的真理,同時將修辭學經過轉化後,靈活運用於教會的牧養與宣講中。正是基於這些需要,奧古斯丁撰寫了第一本講道學教科書《論基督教教義》,為教會提供理論與實踐的指引。
整本《論基督教教義》分為四卷,奧古斯丁在〈卷一〉明確地指出此書是有關處理經文的兩件事:發現[6]需要明白的事情和教導已明白的事情。[7]前者是訓練講道者/教導者如何正確地解讀聖經,這是卷一至卷三要處理問題,寫於395-396年間;後者是訓練神職人員如何適當地運用修辭學的技藝,以提高教導和講道的果效,這是卷四要處理的問題,寫於三十多後年後的426-427年間。[8]
而〈卷四〉的開首也重述全書分為這兩大部分的架構,指出頭三卷是處理「發現」,而〈卷四〉是關乎「教導」。[9] 因此,此書是採用修辭學的觀念撰寫而成,包括從發現至傳講的整個過程,是名乎其實的釋經講道訓練手冊,而不是書名所謂的討論基督教教義的神學教義專著。
因此,許多英文譯本將該書書名翻譯為On Christian Teaching (論教導基督教),以更貼切地反映其寫作宗旨與內容。現時的英文譯本中,兩種書名並存。例如,牛津古典叢書即採用On Christian Teaching作為書名,凸顯該書作為講道學訓練手冊的本質,而非神學教義的論述。[10]
奧古斯丁研究學者、最新英文版《論基督教教義》譯者埃德蒙‧希爾(Edmund Hill) 曾明確指出:「我認為此著作的標題應譯為《教導基督教》(Teaching Christianity)。基督教理當主要透過講道來傳授;因此本書的宗旨在於引導讀者邁向第四卷的目標。然而基督教講道必須以聖經為依據;故準傳道人首先須學習如何詮釋聖經。」[11]
小結
奧古斯丁晚年才完成《論基督教教義》,凝聚了近四十年牧會與講道經驗,成為講道學的經典。此書深刻影響中世紀及後世,至今仍為講道學提供堅實理論基礎,奠定他作為一代宗師的地位。
後記
筆者將於2025年11月8日(六)上午10:00至11:00主講免費線上講座:講道學一代宗師的啟示:導讀奧古斯丁《論基督教教義》,進一步介紹此書的內容和對華人教會講壇的啟發,歡迎報名參加。特別鼓勵正考慮報讀神學課程的信徒參加。詳情參以下連結:「神學線上課堂體驗(實踐神學──講道學)」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1] J. Warren Smith, Forward, in J. Patout Burns Jr., Augustine's Preached Theology: Living as the Body of Christ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22), xiv.
[2] 參雷健生,〈從《論基督教教義》看奧古斯丁如何處理世俗的修辭學與教會的關係〉。神學博士專文。台灣神學院,2021。
[3] 凃偉文,〈從古典修辭學評析新講道學〉,《中華福音神學院院訊》2022年615期,頁6-7。
[4] Hofer, Andrew,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s Serm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5.
[5] James J. Murphy, 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 A History of the Rhetorical Theory from Saint Augustine to the Renaissance (Tempe, AZ: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8.
[6] 「發現」是古典修辭學中inventio的術語,指創作過程中尋找並發掘論點的階段,即尋求和提出可以有效說服對象的論據與內容。奧古斯丁將此觀念應用於聖經解釋過程中,強調在詮釋時需要發掘有力且具說服力的論點。
[7] 奧古斯丁著,石敏敏譯,《論基督教教義》,收《論靈魂及其起源》,北京:中國社會學出版社,2004,1.1.1。
[8] 埃德蒙‧希爾(Edmund Hill)認為這長期擱置是因為當奧氏寫到〈卷三〉第35段時,計劃採用異端多納圖主義者泰哥尼斯 ( Tyconius ) 的釋經原則之前,先寫信給迦太基 ( Carthage ) 主教奧利里烏斯 ( Aurelius ) 取得他的同意。希爾認為可能當時奧利里烏斯沒有正式回覆,或反對奧氏的建議,所以奧氏便把這寫作項目擱置下來。直至三十年後,當他寫《訂正錄》( Retractiones ) 時才記起《論基督教教義》的意義,故此重新完成餘下的部分。參The Works of S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Part I, Vol. 11: Teaching Christianity: De doctrina christiana, intro., trans., and notes Edmund Hill, ed. John E. Rotelle (Brooklyn, N.Y.: New City Press, 1996), 96-97.
[9] 奧古斯丁,《論基督教教義》,4.1.。
[10] Augustine, On Christian Teaching. Translated by R. P. H. Green. Oxford World's Class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 The Works of S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Part I, Vol. 11: Teaching Christianity: De doctrina christiana, intro., trans., and notes Edmund Hill, ed. John E. Rotelle (Brooklyn, N.Y.: New City Press, 1996), 98. 希爾指出拉丁文doctrina的意思非常豐富,可以解作教義或教導,所以按《論基督教教義》的寫作宗旨和內容來看,採用後者的意思更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