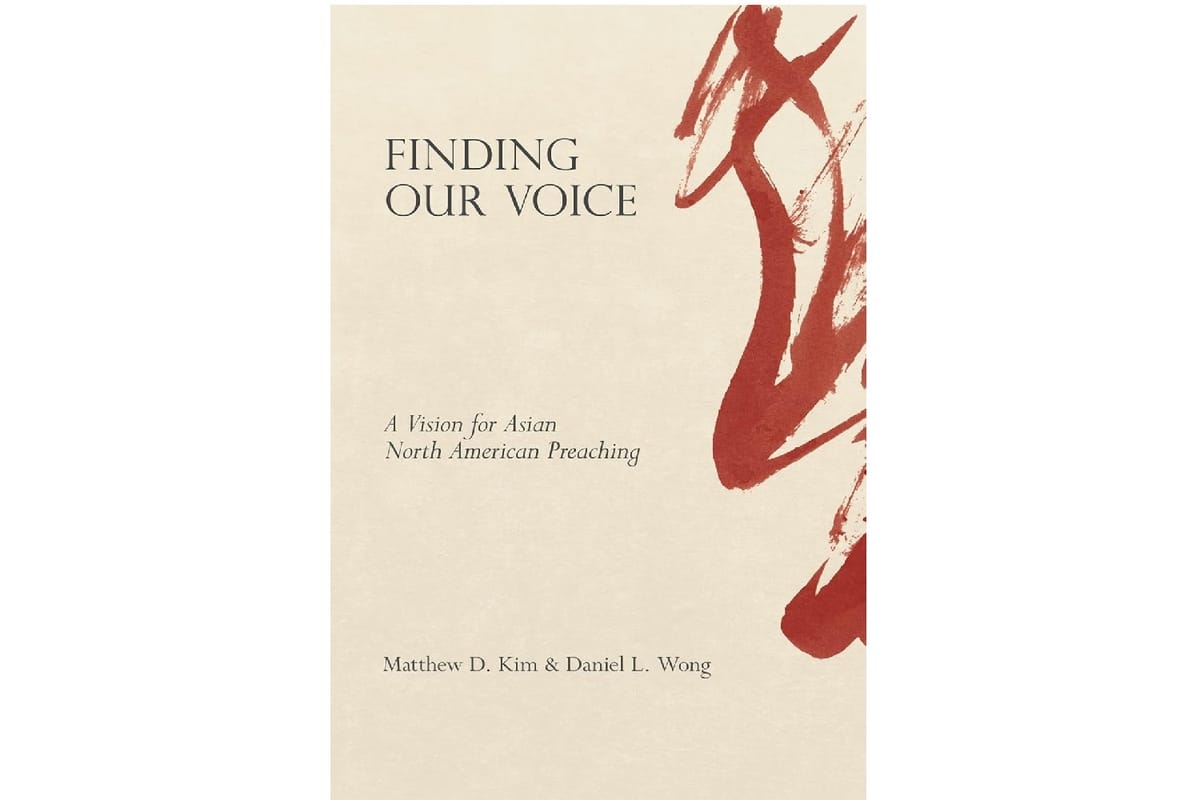當華人教會還普遍認為從北美傳來的西方講道學具有普遍適用性時,我們卻忽略「非西方講道學」(non-western homiletics)早已興起。包括北美的「非裔美國講道學」(African American Preaching)和「亞裔北美講道學」(Asian North American Preaching)。特別是「韓國講道學」(Korean Preaching)的出現。[1]我們不禁要問,為何「非西方講道學」會興起?這是否意味著西方的講道學對非西方教會來說有所不足?
非裔美國講道學的興起與發展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新講道學(New Homiletics)和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思潮的影響下,非裔講道學再次受到學界的重視和認可,突破西方傳統講道學中較為權威和單向的講述模式。非裔講道學起源於奴隸時期,結合非洲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信仰,形成富有情感與群體參與的獨特講道風格。早期黑人講道人多在白人教會中傳道,後期建立獨立的非裔教會。非裔教會的講道強調靈性表達和社會解放,對美國乃至全球基督教講壇有深遠影響,並促進黑人社群的身份認同與精神自尊。[2]
目前北美已經有專門針對非裔美國講道的博士學位課程。例如,安德森大學(Anderson University)旗下的克蘭普神學院(Clamp Divinity School)開設了全美第一個「非裔美國講道暨神聖修辭哲學博士」(PhD in African American Preaching and Sacred Rhetoric)課程,該課程旨在培養教會和學術界的實踐學者,深入研究黑人講道的歷史、神學及修辭傳統,並推動相關學術發展。[3]該神學院也成立了「非裔美國講道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American Preaching),致力於促進非洲裔美國講道歷史和本質的深入學術研究,同時保護和數字化收集過去一個世紀中著名非洲裔美國牧師的講道錄音,建立公開可用的數字資源庫,方便研究和靈感啟發。[4]
亞裔北美講道學的興起
與華人教會文化更為貼近的亞裔北美講道學也正發展成形。儘管目前尚未有專門的哲學博士學位或研究中心,但已有一群韓裔美籍講道學者正致力於此建設。如講道學者金恩珠(Eunjoo Mary Kim)被視為首位以亞裔美國人視角探討講道學問題的學者,她開拓了亞裔美國人在講道、教會生活、學術研究及牧養領導上的重要對話。她的著作Preaching the Presence of God特別強調亞裔美國人在北美基督教會中獨特的文化特質及其對講壇的貢獻。金恩珠目前擔任丹佛伊里夫神學院(Iliff School of Theology)副教授,並持有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講道與神學傳播博士學位。她從亞洲獨特的靈性體驗、詮釋學、傳播方式和修辭策略四個面向,構建出創新的亞裔北美講道學理論框架,甚具啟發性。例如,金恩珠指出,早於基督教傳入東亞地區之時前,儒家和佛家的經典早已流傳於中國、韓國和日本等地,成為當地固有文化的一部分。故她提出可善用這些經典的詮釋進路,來幫助東亞信徒深化對基督教聖經的理解和應用。[5]
另外,有兩位亞裔美籍講道學者金馬修(Matthew D. Kim)和黃丹尼爾(Daniel L. Wong)也正積極參與建構非西方講道學中。前者是第二代韓裔美國人,而後者則是第三代華裔美國人。在其合著的Finding Our Voice一書中,他們指出北美亞裔教會所面臨的文化與身份挑戰是複雜且獨特的。這些教會的成員多為移民及其後代,他們在東西方文化間穿梭,同時經歷著主流白人社會的邊緣化與族裔歧視。此外,他們還需調和代際間的價值觀和語言差異。
因此,要為亞裔信徒創造一個適合其信仰經歷的屬靈空間,存在相當大的挑戰。講道是教會生活的重要部分,必須貼近會眾的文化身份和生活經驗,才能引起共鳴並帶來生命轉化。金馬修和黃丹尼爾意識到,傳統的西方講道學未能充分回應他們在文化認同、族裔經驗和代際差異等方面的複雜處境,導致講道常常難以引起共鳴或對生命產生影響。他們觀察到,許多亞裔講道者受到西方講道理論框架的限制,缺乏能夠反映自身文化背景和靈性體驗的講道學理論與實踐資源,因此迫切需要一套針對亞裔北美文化的講道學建構。
例如金馬修指出在西方/北美神學院受訓的亞裔傳道人通常會認同多種詮釋方法中的一種:例如,歷史-文法模式、正典模式、文學模式、修辭模式、非裔美國人模式或其他種族/文化敏感模式、哲學模式或神學模式等,但卻忽略了考慮一些「被遺忘」的亞洲文化和宗教影響,深深地影響著亞裔北美聽眾和講員對經文的詮釋。如儒家思想強調的「仁」和「孝」,以及後殖民思潮對價值觀和詮釋角度的影響,這些都深刻塑造了他們對經文的理解。因此,金氏和黃氏所提出亞裔北美講道學的建議,包括經文詮釋角度、講道例子選擇、生活應用設計、傳達方式與講道主題的調整。[6]
小 結
筆者認為,非西方講道學的興起正好突顯了建構「華人講道學」(Chinese Preaching)的必要性,這仍是一個有待開發的領域。由於亞裔北美講道學與華人講道學在文化上較為接近,因此更具參考價值。筆者未來將在華人講道學堂進一步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然而,在建構華人講道學時,我們也需要分辨不同地區華人的具體處境和文化特色,例如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華人之間已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必須進行具體分析、比較和歸納。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筆者只能以自身的處境和文化作為起點,尋索華人教會講道的聲音 (finding our voice)。
[1] Jung Young Lee, Korean Preaching: An Interpret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7).此書主要探討韓國教會的講道脈絡、風格及權威,指出韓國講道的獨特特徵以及其對美國教會的貢獻。
[2] Henry H. Mitchell, Black Preaching: The Recovery of a Powerful Art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0), 23-24.
[3] Christ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PhD in African American Preaching and Sacred Rhetoric,” accessed August 30, 2025, https://www.cts.edu/academics/school-of-theology/phd-in-african-american-preaching-and-sacred-rhetoric/.
[4] Clamp Divinity School of Anders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frican American Preaching,” accessed August 30, 2025, https://auministry.com/center-for-the-study-of-african-american-preaching/.
[5] Eunjoo M. Kim, Preaching the Presence of God: A Homiletic from an Asian American Perspective (ValleyForge: Judson Press, 1999), 77-101.
[6] Matthew D. Kim and Daniel L. Wong, Finding Our Voice: A Vision for Asian North American Preaching (Kindle edition; Bellingham: Lexham Press, 2020), chap. 2.